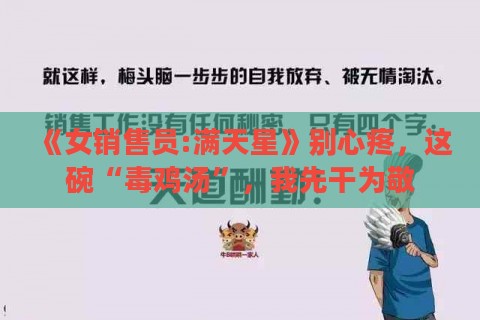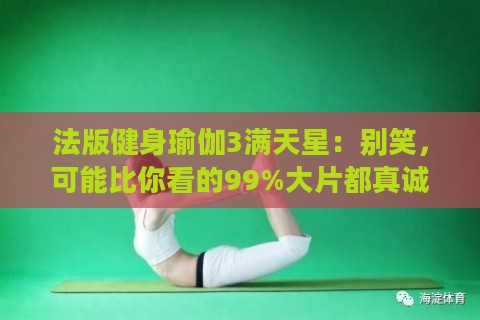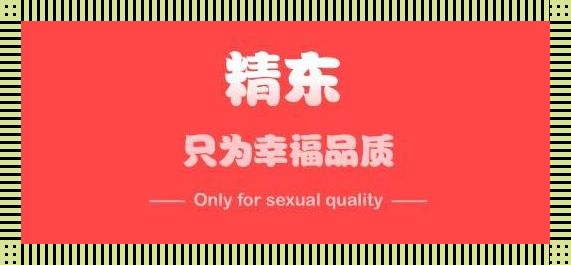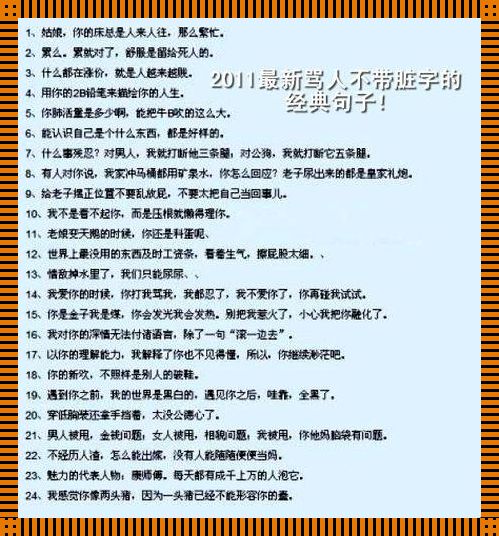说真的,走进影院之前,我对《高压监狱3飞机版》的期待,就像对街边新开的烧烤店一样:不指望吃上米其林,但至少肉得是香的,酒得是冰的。毕竟,二十多年前那架载着尼古拉斯·凯奇和一众牛鬼蛇神的“空中监狱”,是我们这代人的动作片圣经。

结果呢?我坐那看了俩小时,眼看着屏幕上炸得天花乱坠,飞机零件掉得比我的头发还快,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:导演,你是不是把最重要的行李——“人”——忘在停机坪了?
“病毒”的低语,还是“主义”的呐喊?
先聊聊这片子唯一让我精神头起来的地方:反派。
前作的“病毒”赛勒斯,是个纯粹的混乱艺术家,他的恶,是莎士比亚式的,是戏剧化的。而这次的反派,代号“普罗米修斯”的男人,不一样。他一出场,没有癫狂的嘶吼,只有冷静的陈述。他不是为了钱,也不是为了越狱,他要的是通过劫持这架“飞行的巴士底狱”,向全世界直播一场对系统不公的审判。
这哥们儿太懂了。他说的每一句话,都精准地踩在大数据、阶级固化、信息茧房这些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痛点上。有那么几个瞬间,我甚至恍惚了,这劫匪的台词,是不是从哪个深夜的哲学频道扒下来的?他不是个简单的坏蛋,他是个长了獠牙的“意见领袖”。
电影花了大力气把他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、动机复杂的悲情人物。这本该是让《高压监狱3飞机版》超越前作,从一部纯粹的爆米花爽片,升级成一部值得回味的动作惊悚片的绝佳机会。
可惜,导演怂了。
主角,一个长着肌肉的“传声筒”
机会给了,但主角没接住。
新主角,据说是卡梅伦·坡的儿子,一个根正苗红的联邦法警。长得帅,肌肉线条也对得起票价,但他的个人魅力,约等于一杯忘了放糖的白开水。
从头到尾,他的任务就是三件事:皱眉,打人,说正确的废话。反派在那边激情澎湃地输出观点,拷问人性,我们这位英雄的回应永远是:“你这是犯罪!”“快投降吧!”“我会阻止你的!”
我的天,这种台词,AI写作都比他有感情。
他就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NPC,唯一的功能就是推动剧情。你感受不到他的挣扎,看不到他的成长,他爹当年那种为了见女儿一面,神挡杀神、佛挡杀佛的狠劲儿和柔情,在他身上连个影子都找不着。这就导致了《高压监狱3飞机版》评分为什么两极分化:观众冲着动作场面给高分,但只要你对角色稍微有点要求,就会觉得索然无味。
整部电影最核心的戏剧冲突,本该是英雄的“秩序”与反派的“理想”之间的碰撞。结果呢?变成了一个哲学教授在对牛弹琴。
把兔子放回盒子里,但这次没人关心兔子
还记得第一部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吗?“把兔子放回盒子里去。”
那只毛绒兔子,是全片的情感核心。我们知道坡做的一切,都是为了回家,为了那个从未谋面的女儿。所以我们紧张,我们共情。
这一部也想复刻这个“兔子”。它给主角安排了一个急需手术的家人,想以此作为他的行动动机。但这个设定,就像是为了凑单硬塞进购物车的商品,廉价又敷衍。我们从头到尾都没见过这个家人几面,更谈不上建立情感连接。
所以当影片结尾,反派被一拳干翻,主角抱着通讯器喊出那句“我们回家了”的时候,影院里一片寂静。
爽是爽了,然后呢?没了。
那感觉,就像一顿缺了灵魂的豪华快餐。食材顶级,包装精美,吃的时候满嘴流油,吃完了你却只想喝口水,因为肚子里空落落的。
说到底,《高压监狱3飞机版》是一部技术上无可挑剔,但精神上彻底阳痿的续作。它造了一架全世界最酷的飞机,却没想好要往哪儿飞。它请来了一个最有脑子的反派,却配了一个最没劲的英雄。
它最大的问题,不是不好看,而是“不敢”好看。它明明有机会去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,却在临门一脚时,选择了最安全、最平庸的路径,把一场本可能载入史册的“主义”之争,降格成了一场幼儿园级别的正邪对决。
走出电影院,夜风一吹,我甚至记不清主角的脸。脑子里回响的,全是那个“失败”了的反派最后的眼神。
或许,这才是这部电影最大的悲哀:我们竟然更希望那个劫匪赢。